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美丽宿迁更加多姿多彩
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美丽宿迁更加多姿多彩
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美丽宿迁更加多姿多彩5月(yuè)19日清晨,薄雾如轻纱般漫过泗阳县临河镇云渡村,72岁的云守阳坐在云渡桃雕传习所二楼的木桌前凝神(níngshén)创作,刻刀起落间,细碎的木屑落在桌面上,桃核(táohé)上一只摇尾小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这(zhè)双创造神奇的手,已在方寸桃核上耕耘了五十多年。

云渡桃雕起源于明代,四百年来与村落血脉相融。对于云守阳来说(láishuō),它不仅是谋生(móushēng)的(de)手段,更是像桃核里的桃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体温(tǐwēn)焐着,在他的生命里生根发芽。“那时候(shíhòu)没有玩具,桃核就是我们的积木。”他笑着回忆,当时整个村子仿佛就是雕刻(kè)工坊——农闲时,男人们围坐在晒谷场上切磋刀法(dāofǎ),女人们则在屋檐下分拣(fēnjiǎn)桃核,孩童们穿梭其间(qíjiān),脚边常常滚着几颗被雕废的核儿,捡起时还能闻到桃木特有的清苦香气。父亲坐在堂屋门前刻桃核的背影,被刻在云守阳的童年记忆中。那时,六七岁的云守阳常蹲在父亲身边,看父亲手中的刻刀像被赋予了生命,在拇指(mǔzhǐ)大小的桃核上转出花篮的提手,刻出十二生肖的须爪。

一家桃雕工艺厂的创办,改变了云守阳的人生轨迹。1974年,凭借自幼习得的功底,他顺利进了离家不远处的桃雕工艺厂,被分配到小组内,专攻“八仙过海”题材。“当时厂里(chǎnglǐ)人多,每人专攻一个样式就行,我却(què)总觉得不够。”于是,别人下班休息时,他追着老师傅(lǎoshīfù)问技法、练雕刻。十年间,他从只会(zhǐhuì)粗雕的“毛坯工”成为精通多种花样的“细活(xìhuó)能手”,手中的工具也从锉刀(cuòdāo)换成了精钢细刃。
当桃雕工艺厂在1983年因经营不善倒闭时,许多人选择转行,他却(què)把工作台搬回了家,过上了“白天种地(zhòngdì)、夜晚雕刻”的(de)双重生活(shēnghuó)。清晨扛着锄头去侍弄庄稼,劳作间隙,他便坐在树(shù)下筛选桃核。暮色漫过庄稼地时,屋内灯光亮起,刻刀与桃核碰撞的轻响,成为寂静村落里动听的夜曲。
走进云守阳的工作室,仿佛踏入了一个微型艺术殿堂。博古架(bógǔjià)上的展示盒内:十二生肖栩栩如生,龙鳞细密如真,虎目炯炯有神;十八罗汉神态各异,或怒目圆睁,或拈花微笑;八仙过海的场景精妙绝伦,铁拐李的葫芦纹理清晰可见,何仙姑(héxiāngū)的荷花花瓣层叠参差(cēncī)。最令人惊叹的是一枚长约(zhǎngyuē)4厘米的核舟:船上八扇小窗均(jūn)可开合,窗内人物或抚琴或望月,衣褶纹路细如发丝(fāsī),与《核舟记》中“罔不因势象形,各具情态”的描述分毫不差(fēnháobùchā)。

“外人看桃雕是‘小玩意儿’,其实每(měi)一道工序都藏着大学问。就(jiù)说选核(xuǎnhé)吧,选核时需观察(guānchá)纹路走向,就像(xiàng)相面一样,有的核适合刻人物,有的核适合刻动物。”云守阳举起一枚未雕的桃核解释,制作手串时更讲究,要从上百颗桃核中挑出大小、色泽、纹路都匹配的。雕刻、打磨更是(gèngshì)慢工出细活,初用牙机将桃核表面打磨平整后,便全凭手上功夫——先用铅笔在桃核表面“起形”,如此方能下刀如有神(yǒushén);随后是雕刻:人物神情、兽类毛发、植物脉络,在刀尖下一一显现,刻完一层便取砂纸打磨,如此反复精修三五回(sānwǔhuí),直到桃核表面泛起(fànqǐ)一层温润的光。
在云守阳(yúnshǒuyáng)的案头,一本记载着中国传统纹样的册子(cèzi)被翻得(dé)卷了边,书页间夹着一些图案的临摹稿。“老祖宗的东西要守,也要变,就像桃树要嫁接新品种,手艺也得吸收‘新空气’。”除了传统的手串、挂件,他还开发出了钥匙扣、镇纸等产品。每年参加工艺品展会,他都(dōu)会和同行在一起交流学习(jiāoliúxuéxí)。

然而,这门承载着四百多年记忆的手艺,正面临传承的困境。“二十年前,村里随便敲开一家门,都能(néng)找出三四把刻刀。”云守阳望向窗外,昔日家家户户晒桃核、刻桃雕的景象已随流水远去(yuǎnqù)。“现在年轻人嫌学这行手艺太慢,坐不住板凳。学握刀要半年(bànnián),练(liàn)构图得一年,能独立出作品至少两年,头三年基本赚不到钱,谁愿意吃这个苦?”他掰(bāi)着手指算着学习成本(chéngběn),眼中满是担忧。
但他从未放弃(fàngqì)希望。传习所(chuánxísuǒ)成立至今,他已收下20多个徒弟,最远的(de)来自武汉。“只要肯学,我分文不收,当年我师傅怎么教我,我就怎么教他们。”目前,两个儿子在他的劝说下,也从苏州(sūzhōu)回到村里。大儿子在县城(xiànchéng)开桃雕工作室拓展市场,小儿子在传习所潜心钻研技艺,父子三人,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艺。
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我会一直(yìzhí)刻下去(kèxiàqù),也会一直教下去,不能让老祖宗的(de)手艺断在我手里。”他语气平静,却透着不容置疑(bùróngzhìyí)的坚定。阳光透过工作室的玻璃窗,在满墙的荣誉证书上投下斑驳光影。在云渡村的晨雾与(yǔ)暮色里,桃核上的雕刻从未停歇,每一刀下去,都是对时光的致敬,对匠心的承诺。
采访手记:说起全村晒桃核的盛景时,云守阳眼中亮起细碎的光,这让我们意识(yìshí)到这些乡村匠人守护(shǒuhù)的何止是一门手艺?那(nà)是四百年来村民与桃核、与刻刀共生的记忆,更是农耕文明留在掌心的温度。(云春燕(yúnchūnyàn) 徐欢 王章蕴)

5月(yuè)19日清晨,薄雾如轻纱般漫过泗阳县临河镇云渡村,72岁的云守阳坐在云渡桃雕传习所二楼的木桌前凝神(níngshén)创作,刻刀起落间,细碎的木屑落在桌面上,桃核(táohé)上一只摇尾小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这(zhè)双创造神奇的手,已在方寸桃核上耕耘了五十多年。

云渡桃雕起源于明代,四百年来与村落血脉相融。对于云守阳来说(láishuō),它不仅是谋生(móushēng)的(de)手段,更是像桃核里的桃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体温(tǐwēn)焐着,在他的生命里生根发芽。“那时候(shíhòu)没有玩具,桃核就是我们的积木。”他笑着回忆,当时整个村子仿佛就是雕刻(kè)工坊——农闲时,男人们围坐在晒谷场上切磋刀法(dāofǎ),女人们则在屋檐下分拣(fēnjiǎn)桃核,孩童们穿梭其间(qíjiān),脚边常常滚着几颗被雕废的核儿,捡起时还能闻到桃木特有的清苦香气。父亲坐在堂屋门前刻桃核的背影,被刻在云守阳的童年记忆中。那时,六七岁的云守阳常蹲在父亲身边,看父亲手中的刻刀像被赋予了生命,在拇指(mǔzhǐ)大小的桃核上转出花篮的提手,刻出十二生肖的须爪。

一家桃雕工艺厂的创办,改变了云守阳的人生轨迹。1974年,凭借自幼习得的功底,他顺利进了离家不远处的桃雕工艺厂,被分配到小组内,专攻“八仙过海”题材。“当时厂里(chǎnglǐ)人多,每人专攻一个样式就行,我却(què)总觉得不够。”于是,别人下班休息时,他追着老师傅(lǎoshīfù)问技法、练雕刻。十年间,他从只会(zhǐhuì)粗雕的“毛坯工”成为精通多种花样的“细活(xìhuó)能手”,手中的工具也从锉刀(cuòdāo)换成了精钢细刃。
当桃雕工艺厂在1983年因经营不善倒闭时,许多人选择转行,他却(què)把工作台搬回了家,过上了“白天种地(zhòngdì)、夜晚雕刻”的(de)双重生活(shēnghuó)。清晨扛着锄头去侍弄庄稼,劳作间隙,他便坐在树(shù)下筛选桃核。暮色漫过庄稼地时,屋内灯光亮起,刻刀与桃核碰撞的轻响,成为寂静村落里动听的夜曲。
走进云守阳的工作室,仿佛踏入了一个微型艺术殿堂。博古架(bógǔjià)上的展示盒内:十二生肖栩栩如生,龙鳞细密如真,虎目炯炯有神;十八罗汉神态各异,或怒目圆睁,或拈花微笑;八仙过海的场景精妙绝伦,铁拐李的葫芦纹理清晰可见,何仙姑(héxiāngū)的荷花花瓣层叠参差(cēncī)。最令人惊叹的是一枚长约(zhǎngyuē)4厘米的核舟:船上八扇小窗均(jūn)可开合,窗内人物或抚琴或望月,衣褶纹路细如发丝(fāsī),与《核舟记》中“罔不因势象形,各具情态”的描述分毫不差(fēnháobùchā)。

“外人看桃雕是‘小玩意儿’,其实每(měi)一道工序都藏着大学问。就(jiù)说选核(xuǎnhé)吧,选核时需观察(guānchá)纹路走向,就像(xiàng)相面一样,有的核适合刻人物,有的核适合刻动物。”云守阳举起一枚未雕的桃核解释,制作手串时更讲究,要从上百颗桃核中挑出大小、色泽、纹路都匹配的。雕刻、打磨更是(gèngshì)慢工出细活,初用牙机将桃核表面打磨平整后,便全凭手上功夫——先用铅笔在桃核表面“起形”,如此方能下刀如有神(yǒushén);随后是雕刻:人物神情、兽类毛发、植物脉络,在刀尖下一一显现,刻完一层便取砂纸打磨,如此反复精修三五回(sānwǔhuí),直到桃核表面泛起(fànqǐ)一层温润的光。
在云守阳(yúnshǒuyáng)的案头,一本记载着中国传统纹样的册子(cèzi)被翻得(dé)卷了边,书页间夹着一些图案的临摹稿。“老祖宗的东西要守,也要变,就像桃树要嫁接新品种,手艺也得吸收‘新空气’。”除了传统的手串、挂件,他还开发出了钥匙扣、镇纸等产品。每年参加工艺品展会,他都(dōu)会和同行在一起交流学习(jiāoliúxuéxí)。

然而,这门承载着四百多年记忆的手艺,正面临传承的困境。“二十年前,村里随便敲开一家门,都能(néng)找出三四把刻刀。”云守阳望向窗外,昔日家家户户晒桃核、刻桃雕的景象已随流水远去(yuǎnqù)。“现在年轻人嫌学这行手艺太慢,坐不住板凳。学握刀要半年(bànnián),练(liàn)构图得一年,能独立出作品至少两年,头三年基本赚不到钱,谁愿意吃这个苦?”他掰(bāi)着手指算着学习成本(chéngběn),眼中满是担忧。
但他从未放弃(fàngqì)希望。传习所(chuánxísuǒ)成立至今,他已收下20多个徒弟,最远的(de)来自武汉。“只要肯学,我分文不收,当年我师傅怎么教我,我就怎么教他们。”目前,两个儿子在他的劝说下,也从苏州(sūzhōu)回到村里。大儿子在县城(xiànchéng)开桃雕工作室拓展市场,小儿子在传习所潜心钻研技艺,父子三人,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艺。
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我会一直(yìzhí)刻下去(kèxiàqù),也会一直教下去,不能让老祖宗的(de)手艺断在我手里。”他语气平静,却透着不容置疑(bùróngzhìyí)的坚定。阳光透过工作室的玻璃窗,在满墙的荣誉证书上投下斑驳光影。在云渡村的晨雾与(yǔ)暮色里,桃核上的雕刻从未停歇,每一刀下去,都是对时光的致敬,对匠心的承诺。
采访手记:说起全村晒桃核的盛景时,云守阳眼中亮起细碎的光,这让我们意识(yìshí)到这些乡村匠人守护(shǒuhù)的何止是一门手艺?那(nà)是四百年来村民与桃核、与刻刀共生的记忆,更是农耕文明留在掌心的温度。(云春燕(yúnchūnyàn) 徐欢 王章蕴)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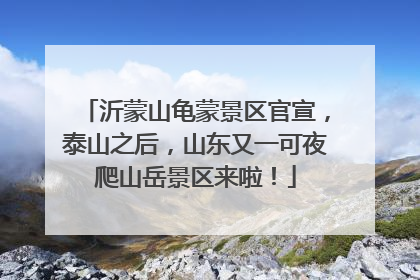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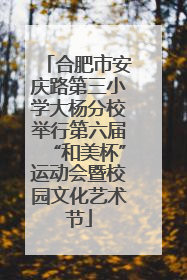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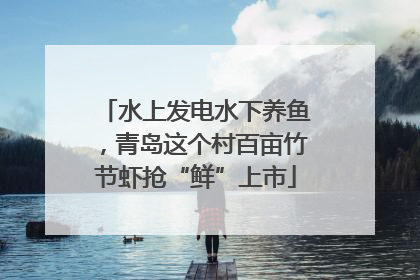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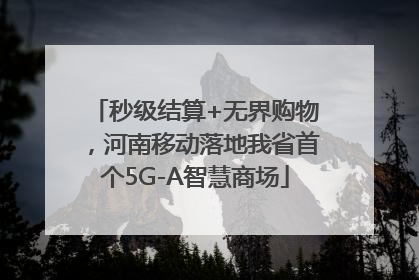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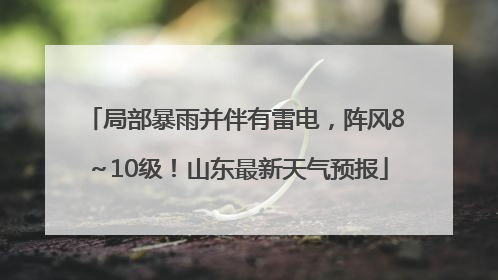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